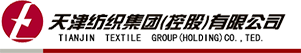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影响复杂深远2020-05-27
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全球快速蔓延趋势,给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复杂影响。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加速累积,一方面,疫情导致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财政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或将引爆相关国家政府债务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扩大贫富鸿沟;另一方面,疫情正在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保守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呈加剧趋势,现有应对疫情的国际合作的有效性备受质疑,全球治理机制面临进一步碎片化的困境。当前疫情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或将导致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交互式”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鉴于此,国际社会应正确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构建“有序全球化”和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多边主义,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在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影响持续深化,国际社会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2020年3月发布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指出,“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深刻表明全球的紧密联系及脆弱性。”全球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现实需要与全球治理能力、机制、资源等方面的不足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此次疫情中更加凸显。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复杂深远,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4月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收缩3%,比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更加严重。为应对疫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了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向极限,但仍然难以有效遏制经济衰退的趋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指出,二十国集团正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作为应对疫情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用以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但是,鉴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其为应对经济下滑推出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竞争性货币贬值。在财政政策领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相继爆发,使得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水平多处于高位,此次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措施,或将进一步诱发政府债务危机。疫情之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刺激计划,两次紧急降息直至零利率,并启动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时美国政府推出高达2.2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计划。但因受疫情冲击,美国股市在3月份的10天内发生了4次熔断,凸显其金融系统中潜在的结构性风险很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其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尤为明显。当前,中国、韩国等国家的疫情已经初步得到有效控制,欧美国家的疫情也有望于近期达到峰值,但印度、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愈发严峻,疫情将对其医疗资源和财政状况造成严重冲击。同时,各国疫情防控进展不一,或将进一步导致疫情在较长时间内形成全球范围的“交互式”传播。为应对疫情冲击,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推出了超强度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持续增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或将导致其陷入财政危机,特别是卫生治理体系较为脆弱的印度、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有可能大幅增加,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在此背景下,相关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可能在特定节点演化为剧烈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增加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加剧部分国家民族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趋势。疫情持续影响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布局。为防控疫情蔓延,许多国家采取了边境管控措施,也使得经济全球化面临新一轮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带来的压力,经济全球化存在失速的风险。同时,相关国家正在重新思考全球化对于本国的影响,对于一些内部反全球化声音高涨的发达国家而言,此次疫情成为其继反对贸易失衡后又一个抵制全球化进程的“重磅武器”。
此次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或将强化各国对全球供应链潜在风险的认知,并加紧推动供应链的本土化进程。各国将越来越青睐外部依赖程度较低的产业政策,尽管这一政策趋势会提高不必要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成本,如美国和中国“脱钩”的势头在疫情防控期间呈现进一步上升趋势。4月7日,日本政府颁布了规模高达108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经济措施,其中包含的“供应链改革”计划中有2200亿日元(约合22亿美元)将用于支持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国内。4月9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也表示,“可以为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成本埋单。”上述举措是典型的去全球化做法,有悖市场经济的逻辑,但对于长期致力于推动本国企业回流的美、日和欧洲部分国家政府而言,疫情引发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调整或将成为其产业链重构的节点性事件。
此外,某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以及污名化的举动值得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利用舆论制造社会恐慌情绪,转嫁国内矛盾和疫情防控不力导致的各种危机。还有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利用疫情鼓吹中国“阴谋论”“威胁论”等,体现了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这种思维认知的影响下,相关国家很难就应对疫情等全球性问题达成妥协,甚至可能促使大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对此,美国国内有声音呼吁,“美国政府应努力避免作出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而且要通过赢得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同,以增强美国的软实力;相反,歧视、偏见和任何过激言论都将摧毁所有的善意。”
三是全球贫富分化态势在疫情之下更加严峻。疫情在发展中国家扩散给全球经济发展和政治合作带来新的挑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恐将引发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政治、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冲击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严重。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应对疫情时尚且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困境,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地区的民众更是连食物和水资源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有能力妥善应对疫情。
当前,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构正在加紧制定保护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也呼吁二十国集团加大对非洲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支持力度,并向非洲国家提供紧急经济援助。如果疫情在上述地区失控,极易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2020年底可能有30多个国家出现饥荒,全球饥饿人口将增加1.3亿,呼吁世界各国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一场全球性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危机的爆发。同时,疫情向发达地区倒灌的风险高企,并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构成长期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已经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也开始转移防控不力的责任,频频要求债权国免除债务等,将疫情政治化的趋势正在上升。
四是传统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治理鸿沟的挑战。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性突发危机,无法完全依靠传统多边机制和框架予以解决。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及其对发展问题的认知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从多边贸易领域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以及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可见一斑。未来民族主义导向的国家政策实践将不断强化,持续侵蚀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意愿和基础,既有全球治理机制将越来越难以回应现实问题带来的挑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全球治理需求与全球治理供给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疫情短时间内急剧扩散突破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极限,导致全球治理赤字恶化为全球治理鸿沟。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看,一些国家的确诊病例数每3—4天就会增加一倍,死亡率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死亡率的10倍,导致传统多边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当前这一全球性挑战。此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发出的声明,虽然对缓和市场恐慌情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如何应对当前全球治理鸿沟挑战,如巨大的医疗物资需求和供给能力短缺之间的卫生安全鸿沟,关于疫情防控的科学讯息与部分国际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的大量负面不实报道之间的信息鸿沟,以及各国政府释放天量货币宽松政策与金融市场巨幅波动难以平息的政策鸿沟等方面,二十国集团却难以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那样发挥关键作用。(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国际合作与路径选择》